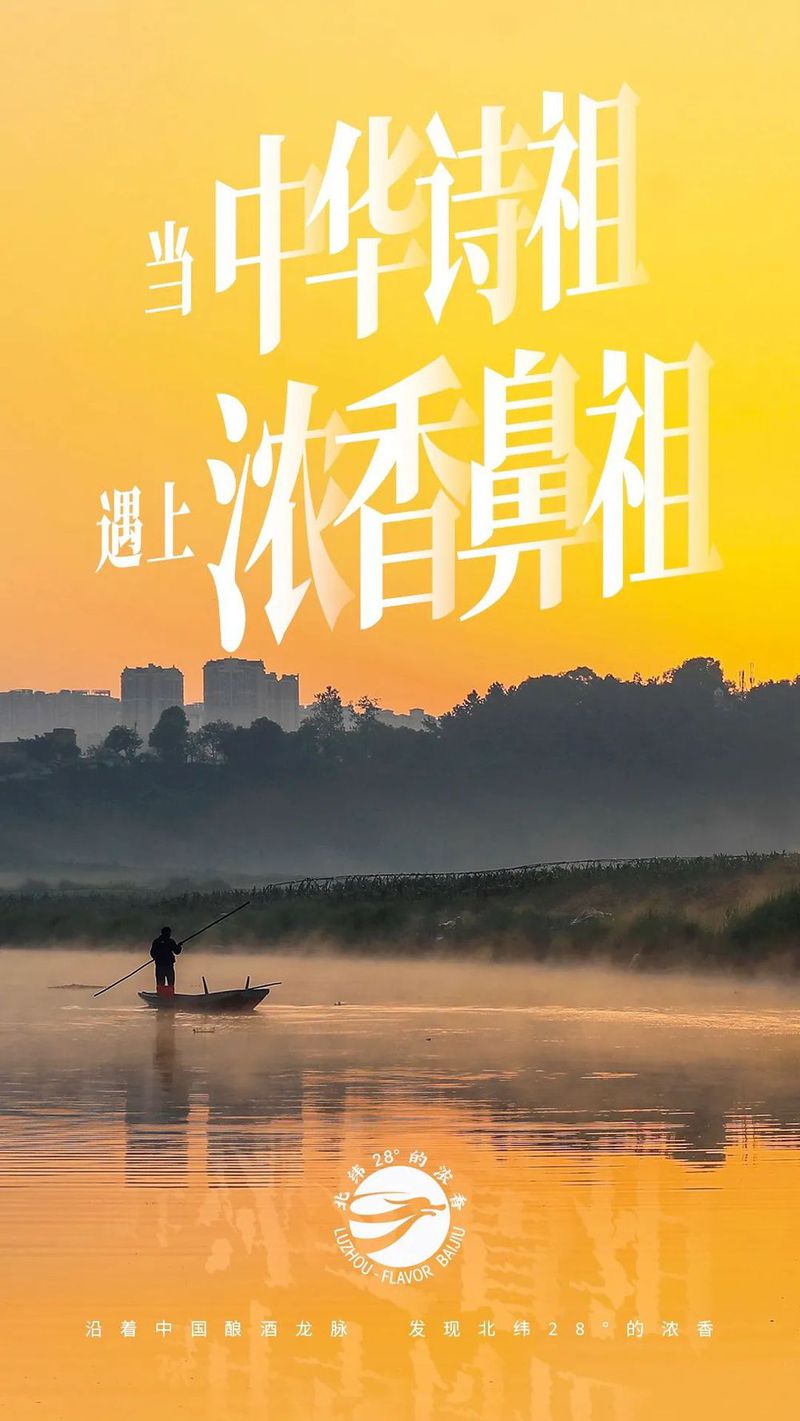
“君来自釜川,我曰渡江口。不看街中花,要饮小市酒。”
“喜看小市小升平,旗亭曲坊人如蚁。”
......
明代诗人杨慎曾寓居四川泸州10余年,在他咏叹泸州的众多诗作中,题咏小市的就占了七首。
由于地域优势和水路运输的便利,小市自古就是泸州的重要水码头。多少文人墨客曾行经此处,饮下泸酒,写下诗作,成为了泸州诗酒风流的重要见证。
经年之后,踏上小市的青石板,再触摸到川南传统民居墙面,仍依稀看得见当年酒铺、饭店、旅馆林立的风采。
 |泸州老窖纯阳洞
|泸州老窖纯阳洞
同样是这一带,在纯阳洞上方林木掩映之间,有一方布满历史痕迹的石台。
相传,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采风者、编纂者和重要作者尹吉甫,其子尹伯奇蒙受冤屈,被父亲放逐于野,便是在这方石台上抚琴,以琴音诉说衷情,编成了琴曲《履霜操》。
曲的末尾带有悲痛的余音,“痛殁不同兮恩有偏,谁能流顾兮知我冤”,娓娓诉说着伯奇的哀思。
后来,伯奇为证清白,自投长江,尹吉甫也终于明白伯奇之罪为人构陷,作《子安之操》追忆。世人闻之,皆被伯奇虽蒙冤屈,仍不变对亲人的至亲至孝所感动。
 |中国国家博物馆《诗经》(来源:视觉中国)
|中国国家博物馆《诗经》(来源:视觉中国)
经历了数年风雨淋漓,这块“抚琴台”已经掩映在历史的长河中,而《诗经》主要采集者尹吉甫与其子尹伯奇的故事,却在泸州长久地流传下来。
尹吉甫被誉为“中华诗祖”,其子尹伯奇则是忠孝文化的代表,二人被浪漫的泸州人传诵千年,正如此处的酒香萦绕不散。
历史的尘烟滚滚而去,随着探知的深入,我们发现,“中华诗祖”与“浓香鼻祖”、中华文脉与中国浓香酒脉都在泸州交汇,如此璀璨,如此夺目。

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尹吉甫也是一位能力拉满的“六边形战士”。
纵览他的大事年表,会发现上面写满丰功伟绩:作为西周著名贤相,辅佐过周宣王和周幽王两代天子,为天子顾命大臣。
他是卓越的音乐家、哲人和诗人,同时也是思想家、军事家、政治家——不仅文能安邦,武亦能定国。尹吉甫曾北征猃狁,南征淮夷,深受周王室倚重,是“宣王中兴”的奠基人。
 |(唐)虞世南辑 北堂书钞
|(唐)虞世南辑 北堂书钞
周宣王以“文武吉甫,万邦为宪”来总结他的功绩,赞其功勋卓著,垂范百官。西周之后,尹吉甫更是成为“忠义至尊”的代表,为后世历朝历代所崇拜。
在中国的文脉之上,也有尹吉甫所绘下的一条重要经络。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采风者、编纂者和重要作者是他;具备“武才”“文才”“治才”三位一体的人物是他;有史记载第一位出川的伟人是他;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伟大诗人,被尊为“中华诗祖”的人,也是他。
 |酒城泸州
|酒城泸州
拥有满腔诗情的尹吉甫,与酒城泸州亦有不解之缘。
关于尹吉甫的“故乡”,学界有几种不同说法,尚无定论。有一种说法称,尹吉甫乃四川泸州江阳(今泸州市龙马潭区石洞镇)人。有关他的传说,星星点点地存留在泸州的史料中。
尹吉甫与泸州的故事,最早见载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
 |(东汉)桑钦撰(北魏)郦道元注
|(东汉)桑钦撰(北魏)郦道元注
该书卷三十三“(江水)又东过江阳县南”条注:“扬雄《琴清英》曰: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后母譛之,自投江中,衣苔带藻,忽梦见水仙,赐其美药,思唯养亲,扬声悲歌,船人闻之而学之,吉甫闻船人之声,疑似伯奇,援琴作《子安之操》。”
这里记载的是尹吉甫放逐伯奇的故事。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教授罗鹭认为,江阳是泸州的古称,扬雄是蜀人,记载尹吉甫父子的传说必然有一定的根据。

宋代之后,尹吉甫在泸州的相关记载和历史遗存变得更加丰富。
北宋初年学者乐史编撰的《太平寰宇记》,在引用《水经注》上述文字时明确将尹伯奇投江之处、尹吉甫作《子安之操》的地点记载为泸州泸川县“黄龙堆”。南宋以后的方志类典籍,如《舆地纪胜》《方舆胜览》《蜀中广记》等,大多沿袭了这一说法。
其中,《舆地纪胜》由南宋中期学者王象之编撰,其中除了记载黄龙堆外,还记载城南有尹吉甫祠堂:“清穆堂,即尹吉甫祠,取‘穆如清风’之义”,“又建清穆堂于报恩观,绘吉甫像焉”。
 |(宋)王象之撰 舆地纪胜
|(宋)王象之撰 舆地纪胜
这清穆堂,是一位曾在泸州做过知州的尹吉甫“忠实粉丝”——陈损之所建。在泸期间,尹吉甫的故事父老相传,热爱诗赋的陈损之自然耳濡目染,颇为感怀,遂为之修建祠堂。
其后,还涌现出几位“忠粉”:在元末战乱中尚不忘为尹吉甫“建祠绘像”的大夏右丞相刘桢,以及清康熙四十六年春刚到任便修缮尹吉甫祠堂的知州朱载震等。
于他们而言,文武双全、忠义之至的尹吉甫是一种精神象征和文化符号,这样的精神也渗入了泸州这座城市的肌理。
 |(清)嵇璜纂 皇朝文献通考
|(清)嵇璜纂 皇朝文献通考
清乾隆年间的《直隶泸州志》记载《忠义祠祝文》云:“致祭于忠义孝弟之灵曰:惟灵禀负贞纯,躬行笃实。忠诚奋发,贯金石而不渝;义闻宣昭,表乡闾而共式。”
这本书卷六《人物志》的序言中,也提到:“泸属自尹氏以忠孝著闻于周,全蜀乡贤,实首太师。自时厥后,朝市递更,士群子或出或处,与阛阓中之娴姆教而励冰操者,纵无考于其全,上下千古,要自有传人焉。”
泸州士子所倡导的忠诚、忠义的品质,与尹吉甫一脉相承。泸州有史料记载的忠义之士不胜枚举,他们的身上,都多少带有尹吉甫的影子。

而从南宋庆元年间设立祠堂算起,泸州人民纪念尹吉甫已经八百多年,直到如今,绵延不绝。穿越千年,酒城泸州的人民,都成了尹吉甫的“知我者”,诗酒之缘缔结得更加紧密。
除了前文提到的抚琴台、祠堂,泸州还有归子山、太师故里坊等地,它们或见于文献,或有遗迹留存于世,成为尹吉甫与泸州命运交织的一种重要见证。

“在这样一个纷纭复杂、充满着不确定性的世界,我们相信诗歌还会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它依然在促进世界的和平、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互鉴、促进我们心灵之间的对话和交流。”
2023年,在泸州开幕的国际诗酒文化大会第七届中国酒城·泸州老窖文化艺术周上,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主任、诗人、国际诗酒文化大会组委会主席吉狄马加如是说。
泸州不仅是一座酒城,还是一座诗歌之城。在国际诗酒文化大会落地泸州之前,这座酒城便早有诗名,而其诗歌基因,最早可以上溯到西周时期。
 |(嘉靖)四川总志 卷十三郡县志
|(嘉靖)四川总志 卷十三郡县志
明朝初年李贤编纂的《明一统志》上,记载了泸州风俗:“家诗户书,勤耕乐输。地少桑麻,刀耕火种。其民淳朴,俗少嚣讼。士竞于文,敦尚儒行。”
这里提到的“家诗户书”中的“诗”,指的便是收录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期间诗歌的《诗经》。
这部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诗歌总集,曾得到圣人孔子的高度评价:“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思无邪,即诚正无邪念。要达到“思无邪”的境界,其一便是作者的态度和创作动机要纯正,其二便是诗歌思想要归于正诚。
这种纯正、正诚,可以从《诗经》的作者尹吉甫身上窥见端倪。
在大多数作者均为“无名氏”的情况下,署有尹吉甫之名的几首诗旁逸斜出,也让其“中华诗祖”的美名当之无愧。
《毛诗正义》认为,《诗经》中有四篇尹吉甫的作品:《崧高》《烝民》《韩奕》和《江汉》。其中没有争议的是《大雅》中的《崧高》和《烝民》。
 |《毛诗二十卷》
|《毛诗二十卷》
尹吉甫将申国的开国君主比喻为高大的山岳,便有了《崧高》:“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
宣王派重臣仲山甫去齐地筑城,尹吉甫赋诗相赠,由此诞生了《烝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
尹吉甫秉一颗赤诚之心,为忠勇之人作诗,歌颂功德,他自己亦是被歌咏的对象。

《诗经·小雅·六月》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又云:“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饮御诸友,炰鳖脍鲤。侯谁在矣,张仲孝友。”
这是庆贺尹吉甫“薄伐玁狁”成功而作的赞歌。“文武吉甫”,是赞美他能文能武;“万邦为宪”,是说尹吉甫可以作为全天下效法的典范;“饮御诸友,炰鳖脍鲤”,则是写尹吉甫在庆功宴上向诸友敬酒。

这一宴会上,必然开怀畅饮、觥筹交错,诗酒文化在尹吉甫身上合流,凝成一缕酒脉的滥觞。
其子所作的《履霜操》以及尹吉甫回应的《子安之操》,也成为泸州诗脉源头。
 |(唐)韩愈撰 昌黎先生文集
|(唐)韩愈撰 昌黎先生文集
或许是文人惺惺相惜,也或许是具有和尹吉甫同样的审美眼光,此后的两千八百多年里,诗人总要为泸州、为尹吉甫父子写文献诗。比如唐代文学家韩愈就曾作《赞〈履霜操〉》,表达对尹伯奇的悲悯之情。
父兮儿寒,母兮儿饥。儿罪当笞,逐儿何为。
儿在中野,以宿以处。四无人声,谁与儿语。
儿寒何衣,儿饥何食。儿行于野,履霜以足。
母生众儿,有母怜之。独无母怜,儿宁不悲。
《赞〈履霜操〉》
汉代才女蔡邕也曾为之吟咏弹奏,至宋朝黄庭坚、曹勋,元朝杨维祯,明朝周瑛,清朝盛锦、李九霞,吟咏者络绎不绝。

开篇提到的杨慎,在《病中怀秋八首·其二》中,也写了“尹氏遗踪百尺台,招呼不见子归来”一句,以此纪念尹吉甫父子。及至清代,诗人张士浩创作了《江阳八景》诗八首,亦有《琴台霜操》。
忆昔啣悲地,乘风蹑操台。菱池空候雁,楟树已非才。
未识履霜调,犹闻杜宇哀。高见无复见,今为立苍苔。
《琴台霜操》
尹吉甫相关,早已恒定地成为文人文思泉涌的素材。此为至诚之人,写至诚之诗。以尹吉甫和《诗经》为代表的诗酒文化,对泸州一带乃至整个巴蜀地区的社会风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美国第一任桂冠诗人罗伯特·佩恩·沃伦曾道:“读完一首诗,如果你不是直到脚趾头都有感受的话,就不是一首好诗。”
英国诗人A·E·豪斯曼抱着同样的看法:“一首好诗能从它沿着人们的脊椎造成的战栗去判定。”
 |(宋)陈仁子辑 文选补遗
|(宋)陈仁子辑 文选补遗
这种身体和精神上的震悚,在尹伯奇的《履霜操》中便可以找到,其诗云:
朝履霜兮采晨寒,考不明其心兮信谗言。
孤恩别离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斯愆。
痛殁不同兮恩有偏,谁说硕兮知此冤。
《履霜操》
该琴曲抒发和寄托的,是一个虔诚孝子对父母永不变易的崇敬、爱戴,以及对自己骨肉兄弟的深情厚意。纵使自己受到了天大的冤屈,此情此心此志,也依然如故。
 |抚琴又名九弦琴,外形似古筝,弹奏时声音节节悲哀、沧桑(图源:视觉中国)
|抚琴又名九弦琴,外形似古筝,弹奏时声音节节悲哀、沧桑(图源:视觉中国)
这首动人的琴曲,源于伯奇“孝子蒙冤”。东汉蔡邕所著的《琴操·履霜操》中,详细记载了这一故事:
尹吉甫娶妻,生子伯奇,后早逝;吉甫又娶妻,生子伯封。伯奇待人温厚仁慈,侍奉后母也至孝。但是后母想将自己的孩子立为嫡子,便设法加害伯奇。
她向尹吉甫说:“伯奇看我漂亮,对我有非分之想。”尹吉甫并不相信,后母便安排他躲在楼上暗中观察。
后母事先捉了几只毒蜂,去掉蜂刺藏于衣领,叫来伯奇,让他帮忙捉蜂。尹吉甫在远处听不清对话,但见伯奇将手伸进后母衣领,于是勃然大怒,不听其辩驳,将伯奇逐出了家门。
伯奇被逐后,离开家到了野外,在古江阳(今泸州市)石洞、齐家、小市等地流浪。
 |霜降为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八个节气,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图源:视觉中国)
|霜降为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八个节气,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图源:视觉中国)
透过《履霜操》,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伯奇清晨踩着寒霜,悲叹自己无罪而被逐,在长江边,伯奇日日“编水荷以为衣,采楟花以为食”。
目睹滔滔向前的长江水,尹伯奇愤而忧伤,遂在江边一巨石上抚琴以鸣心中冤屈,谱成千古名曲《履霜操》。

时间辗转,父亲仍未明白真相,伯奇带着悲愤自投江中。在记载中,跳入江中的伯奇,身上缠满苔藓和藻类,忽然梦见水仙赠送良药,心中想拿回去奉养父母,于是就高声唱起悲歌来。船夫听到,也学着唱。尹吉甫听到船夫的歌声,对伯奇的追悔和无尽思念涌上心头,便抚琴而作《子安之操》,诗云:
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归于周,万民所望。
彼都人士,台笠缁撮。彼君子女,绸直如发。我不见兮,我心不说。
彼都人士,充耳琇实。彼君子女,谓之尹吉。我不见兮,我心苑结。
彼都人士,垂带而厉。彼君子女,卷发如虿。我不见兮,言从之迈。
匪伊垂之,带则有余。匪伊卷之,发则有旟。我不见兮,云何盱矣。
《子安之操》
于中国文人而言,诗歌与音乐俱是他们与世界交流的方式。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春秋时期。《论语·阳货》中,曾记载了孔子的一件小事,“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这里讲的是孔子称病,对人避之不见,使用瑟这种弦乐器,通过弹奏和歌唱的方式,向外界传达了自己的意愿。
取瑟而歌,以曲折的方式表达情意,伯奇的《履霜操》亦是如此。在尹伯奇身上,我们见到古老的诗性,映照出中国的心灵。

清朝的王士祯于康熙十一年(1672)以户部福建司郎中的身份典试四川,回程时走川南水路,于十月初五日留宿江阳(泸州),此间,便夜游抚琴台,有所感怀,作有《抚琴台(一作渡)》。
明月生琴渡,如闻弹履霜。猿声何处发,今夜宿江阳。更有巴渝曲,能沾旅客裳。枫抹前路远,叶叶似潇湘。 《抚琴台(一作渡)》
诗以抚琴台所见所闻为背景,抒发了淡淡的羁旅之情,与同样想回到家的尹伯奇产生了共鸣。

李九霞是康熙年间富顺人,同样到访抚琴台,留下“明月不知千古痛,余光犹在照琴台”的佳句。这首诗是更为直接的凭吊诗,尹伯奇的遗憾似乎可以透过悠悠明月,照到后人身上。
康熙年间泸州学正高之傅撰写的《琴台霜操》,提到“大孝生来遇每奇,太师有子未能知。想当抚背挥弦曰,如对深山号泣时。解愠已成千古圣,履霜仅惜数行词。空台历落堪凭吊,哀思凄然寄水湄。”

自西汉以来,代代文人来此凭吊,莫不为尹伯奇的拳拳孝心动容,留下许多哀思。不仅如此,文人们将对世事的感慨,对忠孝两全的尹伯奇和大义凛然、勇于纠正自己错误的尹吉甫的赞美,都留在了泸州。
历代泸州人民,皆以“文武吉甫”“孝子伯奇”为榜样。这种忠孝一体的思想,也演变为泸州地域文化的一部分。

宋开禧二年,泸州知州(旧题魏了翁)撰写的《重修州学碑记》中说:“故古志谓泸俗好文雅,又重以太师吉甫文武宪邦之忠、伯奇援琴履霜之孝,其所熏渍,质实而近本。士生其后,理义精明。”
吉甫之忠、伯奇之孝,在泸州历朝历代加以渲染和发展。一代又一代的泸州人,秉持这两种文化传统,勤劳质朴,敦尚文雅,忠诚报国,孝悌传家,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

而泸州文雅的风尚,大概在《诗经》时便埋下了种子。
尹吉甫采风、编纂集结的《诗经》中,有多处出现了酒的身影。
《早麓》中有“瑟彼玉缵,黄流在中”,“黄流”是酒的别称;《韩奕》中有“显父饯之,清酒百壶”;《南有嘉鱼》中有“南方有好鱼,群之游水中,主人有好酒,宴会宾客乐无比”的劝酒歌;《小苑》中有“人之齐圣,饮酒温克”;《鹿鸣》中有“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宾之初筵》中有“酒既和唱,饮酒孔偕”。

尹吉甫是爱酒之人,自然也尝过泸州的酒。
温暖湿润的自然环境、饱满挺拔的高粱,还有数十条河流的浸润,织起交通的密网,让泸州成为天选“酒城”,酒文化也在此蔚为大观,渐渐催生出“浓香鼻祖”——泸州老窖。

700年来不曾断代的浓香酿造技艺,亦为泸州不断汲取风华、愈加丰饶的见证。
如同泸州现今多处道路以酒城命名,泸州人对诗祖尹吉甫和孝子伯奇亦是念念不忘,曾用“琴台霜操”替换“荔林书锦”,入了泸州老八景。
还有多处地名留有尹氏父子的痕迹:泸州龙马潭区有座尹吉甫学校,小市半边街居民的安置小区名为抚琴山水、鱼塘街道下辖抚琴台社区、龙马高中背后干道名为琴台路、泸州电视塔下有条抚琴街……

“中华诗祖”与“浓香鼻祖”,在泸州传承至今,皆是泸州的精神财富。
自尹吉甫始,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徜徉于泸州的山水风物,宴饮之间,留下众多名篇佳作,将富庶、繁华的泸州烟火气永久地留于纸面。
“自古诗人例到蜀,好将新句贮行囊。”这座诗酒之城,容纳了文人的风骨和气节,让尹吉甫父子的故事代代传颂,也许这便是“中华诗祖”与“浓香鼻祖”命中注定的相遇、相知、相守。
参考文献:
- END -
来源于公众号-北纬28度的浓香,本文略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