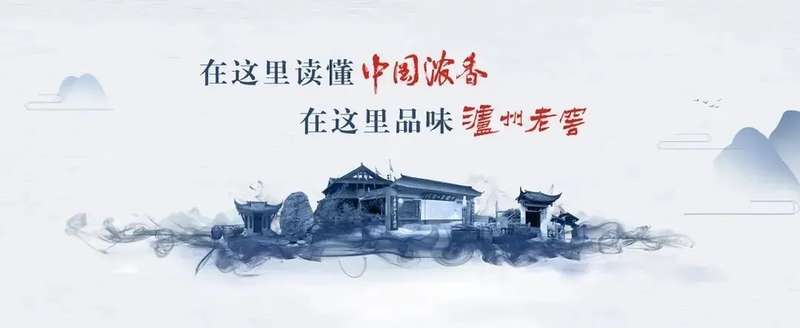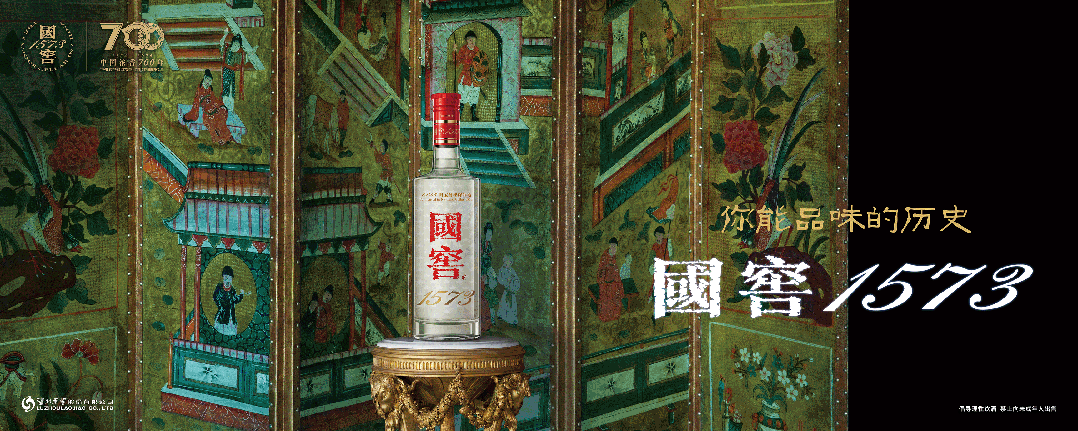根据人类史学家的研究,在人类进化过程中,酒至少有两次重要的历史关头拯救了人类,或者说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众所周知,地球历史上大约经历了五次大的冰期,距离最近的一次,又称“第四纪大冰期”,大约始于距今200~300万年,结束于2~5万年前。大冰期时期,大部分纬度带被冰川覆盖,当森林被草原和冰川取代,当获取食物已经不再那么容易,生命物种的灭绝和被迫的基因改变,是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如同恐龙类大食量的动物不得不因为缺少食物而灭绝,而人类的祖先——类人猿(或此时已进化成早期智人),也不得不改变自己的食物结构,从原先的只“挑食”新鲜的果子,到不得不适应烂果子的气味和天然发酵出来的乙醇。
因此,对乙醇的分解消化能力,就决定了类人猿的食谱范围扩展,而处于大冰期时期的食物匮乏期,每增加一份食物的供给,就决定了多一分生存机会。
动物体内乙醇的代谢能力取决于乙醇脱氢酶(ADH4)的含量,乙醇脱氢酶含量越高,代谢能力越强,反之,代谢能力越弱。在一项研究中,科学家们检测了28种哺乳动物体内的乙醇脱氢酶含量,发现,大约在近1000万年以来,从类人猿到智人对乙醇的代谢能力至少提升了40倍。因此,可以说,是那一部分本身具有较强的乙醇代表能力的猿猴生存了下来,并在后续的进化过程中,不断通过基因改变,获得了更强的乙醇代谢能力,从越来越难以获得的果实和酒精中获取卡路里,让人类的祖先艰难地渡过了食物匮乏的冰期时代。酒带给人类的第二次变革是酒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人类从游牧文明进入了农耕文明时代。如前述所言,酒诞生的历史远远早于人类的历史。酒,初为天酿,自然发醅,后为人工改良,曲糵入酿,不断提升发酵效率和改善酒的口感风味,乃至后续蒸馏技术的使用,才是人工参与的结果。因此,准确地讲,是人类发现了酒,而不是发明了酒。中国历史传说中,无论杜康酿酒还是仪狄酿酒,都只能说明杜康、仪狄等在人工改良这一过程中起到了突出的作用,用今天的话来说,无论仪狄,还是杜康,相当于最具代表性的“中国酿酒大师”或“国家级酿酒非遗传承人”。“吃饭实在是从饮酒中带来的”。我国考古学家吴其昌博士和美国人类学家索罗门·卡茨几乎在同一时期,持有这个观点。在人类进入农耕文明以前,谷物类、果实类食材并不是人类的主要食谱,那时,人类尚是以游猎,猎取动物肉类食材为主。肉类食材的生活习性决定了当时的人类或许并不一定要进入农耕文明。然而,此时已经习惯了“饮酒”的人们却不总是能够轻易的获取自然界天然酿造的酒,当天然野生的果子或谷物,无法满足酿酒需要的时候,人们开始有意识的种植粮食,即所谓的“为饮而种”。2018年,英国考古学家在距今约1万-1.4万年前,作为世界三大农业起源地之一的,位于约旦的纳图夫文化遗址发现了酿酒的遗迹,而纳图夫文化遗址是西亚地区正处于采集社会进入农业社会的过渡阶段,这一考古发现,至少说明酿酒与人类农耕文明的形成是相伴相生,或互为促进的。我们国家距今约9000年前的贾湖遗址的考古发现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果说地球上曾经历过多次文明的更迭,那我们这一轮文明可以说是“因酒而生的文明”。从此,酒与人类文明相生相伴。酒是生活必需品,“何以解忧,唯有国窖”;酒是生活方式,“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酒是生活态度,“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酒是生活理想,“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最后,酒构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